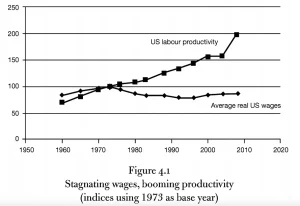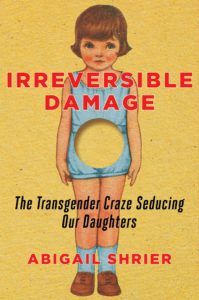
书评
“Irreversible Damage : The Transgender Craze Seducing Our Daughters”, by Abigail Shrier
我不是trans-activist,我也不认为每个自认是trans的青少年都是天生trans,都会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坚定地自认trans,甚至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最终的性别认知会变回生理性别。我认同作者的部分说法,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与她分歧巨大。我赞同她在第四章提到的,也是radfem常说的,整个trans文化建立在生理性别和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有着对应关系的假设上,而这个假设正是女权主义者要打破的。尽管我和她都赞同这一理论的抽象表述,但是我发现,一旦涉及到理论落地,就是需要她分析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时候,她立马显露出牢固的性别刻板观念。而且,我也十分厌恶她每次提到青少年的那种轻视、不屑的态度。她的采访稿信息量很丰富,采访对象包括了trans的父母,支持和反对affrimative care的专家,transitioned和detransitioned的亲历者,她梳理了对这些不同视角的意见,让我学到很多。但她的个人见解常常充斥着傲慢和肤浅。
这本书看似反trans,其实很多地方作者表露的观念体现出的深层文化,正是孕育了trans运动的环境动因。她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书中多处展现出她陈腐的性别观念,而且是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被说出来,可见这些观念都被她完全内化了。比如,她提到某FTM网红晒自己第一次购买束胸的经历,那人在视频里戴上束胸后兴奋地尖声说,这是她人生最棒的一天。作者评论说:
Breasts may be painful reminders of one’s birth sex, but apparently shrieking is not.
更直白地翻译一下,她的意思是,这个FTM,表面上说自己是男性,但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尖叫了起来,完全忘记了只有女性才会尖叫这件事。她的评论中很显然对尖叫这件事抱有轻蔑的态度,然后她又把尖叫限制为了女性专属的特点,也就是说,她暗示,某个只有女性才有的特点令人鄙视。首先,男性激动的时候也大喊大叫,音调多尖算尖有待商榷,第二,她轻蔑的态度让我愤怒。
除了性别观念落后,作者还有另一个社会通病:她认为女性身体的被使用性要高于住在身体里的灵魂对身体的主权。我认为,这种影响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文化观念,正是把年轻女孩推向trans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子就是,她讨论穿束胸对年轻女孩胸部发育的危害,延伸到以后有了孩子会影响喂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话语的猥琐。
But try convincing a teenager that something she wants to do carries risks. Imagine telling her that she might not want to damage her breast tissue; that she might one day want to have children and, having birthed those children, to nurse them. It’s a little like informing her the sun will burn out five billion years in the future.
作者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体里过自己的生活,只有身体的主人有权选择怎样使用自己的身体。她觉得女性因为要做“未来的母亲”,所以身体应受他人的监管。只要监管的出发点貌似正当,比如“为了孩子”,监管人就理所当然地攫夺了控制年轻女性身体的权力。后面她举了自己的例子,大一时为了穿衣服好看,想做缩胸手术,被父母劝阻了,后面遇到了“那个正确的人”,生了三个孩子,体验到母乳喂养是最棒的和孩子建立连接的经历,于是庆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那个手术。翻译一下,她的心路历程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的被展示性(展示给男人看)最重要,年纪大了以后,觉得身体的被使用性(被孩子使用)更重要,这就叫从一个大坑走进另一个大坑,从展览品到营养品,哪个功能也无关身体独立存在的价值。
她自以为站在未来的孩子立场上,就高出了任性妄为的年轻女性一头。为了孕育”更健康的孩子“,女性就应当让渡身体主权吗?其实恰恰相反,驯服于这套权力话语,任由别人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女性,会成为最差的母亲。连身体自主权都没有,作为人的精神已经残缺了,长几个乳房有什么用。说句不好听的,猪圈里的猪长了十几个乳房,生的小猪还不都是任人宰割吃肉。失权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必然重复她失权的命运。
作者认为许多trans-identified teenage girls并没有gender dysphoria,而是受到了社交圈子的影响,觉得成为trans很酷。很多人十几岁时接受了性别纠正治疗(束胸、荷尔蒙等等),几年以后想重回生理性别时,身体已经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没有试图否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悲剧性,也不否认现在的解决方案存在种种缺陷。我反感的是作者展示问题的方式,她评论的态度,少有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她轻视青春期的挣扎,把少年的困境都归结于浅薄和轻浮。在我看来,她自恃为他人生命健康的保护者,但是根本不了解生命的需求,生命不是提线木偶,不会沿着某条“正确”的路径行进。
在我理解中,青少年的性别迷惑,其实是她在经历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特别是这个社会,到处都是把僭越、侵犯年轻女性身体主权当成常态的人,女孩总是更多地面对这个困境: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试图限制、规划、控制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真的属于我自己吗,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完全拥有我的身体?她在和父母、和社会观念斗争的过程中,想要争得的是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有些人认为,青春期女孩不该接受雄激素注射,因为“她们的子宫还要生孩子”,青春期女孩不该做乳房切除,因为“她们的乳房还要用来喂奶”,青春期女孩不能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因为她们长大以后才会懂得自己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对“未来孩子”、“未来爱人”的欠账。正是这种把女性身体和她的精神相隔离的文化观念,把青春期女孩推向了trans阵营,正是这种观念,让trans-identified青少年觉得来自作者那一辈的父母“toxic”,甚至跟父母决裂。
如果你说,affirmative care不合理,是因为它完全依赖于未成年人的自我诊断,而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心智去评价手术风险、足够的能力去承担性别重置的后果,这我完全赞同。但是,一件坏事,比如affirmative care,也不能用错误的理由去阻止它。“女人的身体不能由自己处置,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影响着你的亲密关系,影响着你的后代”,这就是错误的理由。
在几个desist的案例中,家长带着性别迷惑的女儿休学一年,四处旅行,还有一个母亲把女儿送到马场工作了一年。这些教育的成功,在于它们通过增加未成年人和环境的互动,通过让她参与有真实影响力的创造性活动,弥合了她的精神和身体间的裂痕,加强了她对身体的控制感。这种教育是有益的,滋养的,这才应该是教育的方向,而不是向青春期女孩重复关于性别和身体的陈词滥调,试图弱化、否认女性的主体意识。
未成年人终会有成年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她将会获得完全的身体自主权,并且承担完全的责任。人将完全拥有自己的生命,而行使完全的权利代表着承担全部的风险。需要承认,这个时刻必将到来。对未成年人的种种培养和教育应该为这个时刻做准备,而不是否认这个时刻的存在。谁能决定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值得赌上生命,生命就属于谁。压抑生命的冒险,必然导致生命的窒息。
我对FTM trans运动的同情之处在于,我感到,在很多时刻,这是年轻女孩对于企图控制她身体的社会压力的拼死抵抗。我保留意见的部分在于,首先,我不认可“喜欢画画、跳舞的是女性,喜欢运动、电子游戏的是男生”这种无理无脑的角色强加;第二,我感觉随便地设定自己的identity,其实是种心理健康上的高危行为,几乎类似于没有经过训练就去高空走钢丝,许多人还意识不到自己在高空走钢丝。作者其实短暂地触碰了这个观念。她提到,心理学观察早就发现,青春期的女孩很容易对同性萌发恋情,过了青春期许多人又变回异性恋【1】。上一代经历这些的时候,只把它当成一个阶段,而这一代则要把每一点情绪、每一次恋爱,都分类,诊断,变成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Were it not for this compulsion to categorize and diagnose, minor bouts of anxiety, depression, obsession, romantic impulse, sexual inclination, and all manner of good and bad feelings might be left to grow, develop, change course, or die off.
由此延展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往自己身上贴标签“我是XX人”的行为背后蕴藏的风险,被大大低估了呢?因为,身份关系着你的从属,而从属关系着你的生存【2】。如果一个人把随便什么东西都加到自己的身份里面,“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我是马拉松跑者”,”我是个同/异/双性恋”,那他就把这些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变成了性命攸关的事。于是改变饮食、改变锻炼习惯,改变恋爱对象,全都变成了生死抉择,这会让生活变得非常艰难。这也是为什么自称是“XX者”的人,总给人一种好斗的印象。外人看来的一件小事,因为关系到了identity,变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表现得激动、愤怒、那么不顾一切地反击,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性命。
我不是说,人不能认同自己的任何身份,而是说,选择性地考量,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加到自己的identity里面去。这个世界上傻X加扯淡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要挨个斗争,几辈子都斗争不过来,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要精挑细选,哪一件事是我的使命,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最有价值的事情中去,用只有一次的生命捍卫最值得捍卫的东西。其它的事情,就让它们停留在从心选择的层面,保持它的随意性:我今天选择了去训练长跑,过去的五年选择训练长跑,但是也许未来有一天我突然就选择不再长跑了。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自由我永远保留。我觉得这种心态,类似于作者说的“left to grow, develop, change course, or die off”,也是我赞成的心态。
我觉得,trans运动,能在十年左右获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动量,有其迎合父权制性别模板的原因,更有一部分原因是它触发的心理危机=身份危机=生存危机,而人在生存威胁下,爆发出的求生本能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但辩证地来看,使人刚强者,也使人脆弱。人在保护自己的死穴的时候能爆发出超人的能量,但是这种爆发对生命力是一种透支,而且死穴的数目越多,人只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难以生存。给自己贴的标签越少越好,不要自己给自己制造阿喀琉斯之踵。简装上阵,更散漫,更自由,更有活力远途旅行,更有闲情游游逛逛,观赏路边风景。
【1】Adrienne Rich begs to differ。她认为“变回异性恋”往往反映着女性屈服于父权制的洗脑和暴力。出自《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2】原文是Identity is key to inclusion, and inclusion is key to survival. 出自《Gift of F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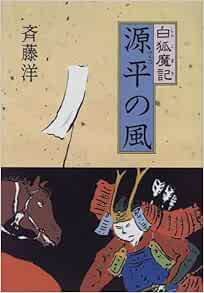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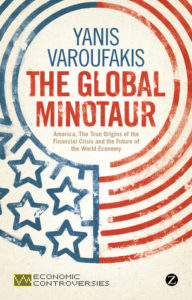 书评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