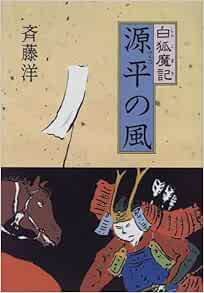书评
书评
《霧のむこうのふしぎな町》,作者柏葉幸子
最近看了一些日本儿童文学,结果让我心情很抑郁。按理说儿童文学应该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然而只能说表象如此。细看之下,这些故事得以成立的前提所展现出的儿童的处境,与其说是自由无拘束的,不如说是恰恰相反。
儿童被投入这个世界之后,就不得不接受一切迎面而来的东西。成年人不满意现状可以拒绝,可以远离,可以造一个茧房屏蔽外界,可以动用武器保护自己。而儿童对自己的生活是基本上失控的,既不能选择生存环境,也不能选择生活方式,更不能拒绝来自成年人的管束。儿童只有等待的命运,她被人从一个环境带到另一个环境,被安排着做这一件事和下一件事。没有人带走她,她就无法离开,有人要带走她,她就无法留下,这其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令人窒息。
即使是在小说里,儿童也没有力量主动选择进入或离开冒险地。冒险故事的主角往往在无意中踏入了一个秘密仙境,她的停留时间通常已被规定好了,但她对此一无所知,她开心地享受探险的快乐,直到在某一刻被突然通知需要离开。比如《霧のむこうのふしぎな町》里,主角Rina追逐被风吹跑的雨伞时,误入了雾中小镇。她被Pipity婆婆安排到镇上的几家魔法商店帮工,和镇上的居民成为了朋友。几个月之后她突然被Pipity婆婆告知已经到了要离开的时间了。她想知道明年能不能回到雾中小镇时,Pipity婆婆并不正面作答,反而故意把雨伞藏起来,让她误以为被拒绝了。在她伤心地打开朋友们的送别礼物时,看到了放在最下面的雨伞,又高兴了起来。可是她的高兴和失落,是多么不由自主啊。情绪的起落成因,与她个人的行动无关,只是受了成年人的逗弄罢了。
在儿童本身的弱势处境之上,还有日本位阶尊卑文化罩下的阴影。在一类常见故事中,主角一开始就被抛入了陌生地,对此地的规则懵懂无知,这时她遇到了一位前辈,一位向导,帮助她探索适应新环境,教导她这里的生存智慧。这种师徒设定当然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独有,但师徒相处模式中的权力色彩确是日本独有的。在《白狐魔記》中,狐狸作为仙人的弟子向仙人求教问题,有时没有听懂仙人的答案,或因为仙人故意语焉不详,或由于理解偏差。然而狐狸却不继续追问,而是自己绞尽脑汁地猜测,仙人则看着狐狸抓耳挠腮的神情或者猜错后做出的傻事以此为乐。类似的相处模式也存在于Rina和Pipity婆婆之间。
如果主角和导师仅是师生授业的关系,学生何必需要闷声揣摩老师的弦外之意,未尽之言?换句话说,在这种权力模式中,徒弟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猜测师傅,而师傅却没有义务让自己变得更容易理解。师傅让徒弟猜测自己的心意,并非出于启蒙开智的目的,而是在主张他凌驾于徒弟之上的权力。
只有下位者对上位者,才需要左思右想地揣摩上意。揣摩结果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取悦上位者的是下位者努力揣摩本身。或者不如说,上位者最乐见的是,下位者为猜测自己的意图殚精竭虑辗转反侧,最终却依然猜错了。如果总能猜中,反而引来上位者的厌恶和忌惮,就像杨修说破曹操心思之后一样下场悲惨。
上位者不只要用权力强迫你遵循他的意志,他更追求让你从心底里认同他的逻辑。而他并不采用一套固定的逻辑,更遑论公正,他的规则随时可以为适应他的利益而变化。Rina刚到小镇时,Pipity婆婆让她去镇上工作赚钱付生活费。Rina说自己有零用钱,Pipity婆婆问那是你自己赚的吗,Rina说不是,是家长给的,Pipity婆婆说既然这个钱不是你自己赚的,就不能用。于是Rina被说服了,接受了去书店的工作安排。要我说,用“不劳动者不得食”威胁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是彻底的流氓行径,强买强卖。她依赖你,所以欠你的吗?她没有在社会上赚钱的能力,被说成是她的缺陷一样。为什么不问问,是谁让她陷入这样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你的境地的呢?是谁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用雨伞、大风和雾气把她骗过来了呢?儿童文学里的这些情节,到处流露出成人世界的傲慢。等到成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又闭口不谈独立了。Monday和老婆Kinu在教育孩子Sunday的问题上起了争执,打了老婆一巴掌,把老婆气走了,之后他和Sunday两个人吃糖不知节制,长了蛀牙很痛苦,Kinu从Rina那里听说了之后,放心不下让父子俩独自生活,就又搬回去了,结局母子团聚,皆大欢喜,Pipity婆婆也默然赞许。为什么这个时候Pipity婆婆又不来指责Monday和Sunday不够独立了呢?做不到保持牙齿清洁的成年人理应有人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而六年级小学生应该自己劳动赚钱自己花,这不是流氓逻辑,什么能算流氓逻辑呢?
当儿童文学忠实地描绘儿童的处境时,奇异地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即使在为儿童而写的文学作品里,她也难以被当做是个平等的人来看待,她被引导被保护甚至被宠爱着,但时常不被尊重,永远不会被畏惧。《ルドルフとイッパイアッテナ》里,虎斑猫易白易阿特那为了给徒弟黑猫鲁道夫准备践行宴,愿意放下脸面去求仇人施舍一些牛肉,结果被打成重伤,然而这样宠爱徒弟的易白易阿特那,之前只是因为鲁道夫说错一句话,就狠狠打了他一个巴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宠爱,也是他霸权控制的一部分。即使再被宠爱,仰仗别人鼻息的生活,整日担心供养人突然死掉或者翻脸,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平静安定的生活随时有被意外打断的风险,她无力影响外因,却要承受成年人一切行动的后果。如果没有为儿童权益撑腰的公共机构,她在自己的家庭里,该是多么孤立无援啊。
我好多年没读过儿童文学了,最近集中读了几本之后积累了某种直觉性的憋屈,整理了下思路絮叨成文,主要是为了让自己记住现在的这种感觉吧。我怕后面类似题材读的越来越多,大脑逐渐内化了其中的逻辑,不再有不舒服的感觉,对新鲜接触时眼前很显然的东西反而视而不见了。也希望能读到更多的平等对待儿童,赋予儿童力量的文学故事。